德国物流从业者:美关税政策多变 企业适应“非常困难”
德国物流从业者:美关税政策多变 企业适应“非常困难”
德国物流从业者:美关税政策多变 企业适应“非常困难”5月24日,伦理(lúnlǐ)与文明国际会议(huìyì)在南京召开,会议期间举办多场专场会议,全球专家学者围绕关于(guānyú)伦理的(de)(de)子话题展开研讨。在“伦理与新兴科技文明”专场会议中,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山西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着人工智能兴起衍生出的科技伦理治理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共同探讨技术狂飙时代下的伦理挑战与文明走向(zǒuxiàng)。聚焦“人类主体性”“价值对齐”“中国方案”等关键词(guānjiàncí),为(wèi)科技与伦理的共生提供了多元视角与理论(lǐlùn)路径。

人工智能类人(lèirén)化?探寻科技的伦理限度
在专场会议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jiàoshòu)王国豫以“实验伦理学”为方法论,提出了大语言模型(LLMs)的“道德生长模型”。她指出(zhǐchū),GPT系列模型从GPT-2到GPT-4的迭代中,其道德判断能力随参数规模(guīmó)增长(zēngzhǎng)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与杜威的“冲动-习惯-性格”道德发展理论(lǐlùn)存在相似性。

通过构建(gòujiàn)“打人”场景的三(sān)维度测评(cèpíng)问题库(道德(dàodé)认知、困境判断、行为选择),王国豫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发现,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为模型提供了类似人类社会的“道德生长环境”,使其能够通过训练逐步习得“善言”。然而,模型缺乏理性能力与(yǔ)(yǔ)真实情感,仅能形成“道德习惯”而非“道德性格”,导致其易受误导或在复杂场景中失效。王国豫强调:“技术对齐的局限性表明,外部监管与社会治理仍是确保AI伦理安全的基石(jīshí)。”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xuéyuàn)教授田海平从存在主义视角切入,揭示了AI“类人化”背后的伦理危机。他指出,当AI在自主决策中无限(wúxiàn)逼近人类时,可能引发“主体性僭越”——机器重构的“它世界”若(ruò)脱离人类价值底线,将(jiāng)动摇文明根基。

为此,田海平提出三条伦理禁令:生存性整体性禁令、生存性实例性指令、生存性独特性律令,即机器不可(bùkě)(bùkě)完全“代理”人类(rénlèi)、机器不可完全“替代”人类欲望、机器不可将人类“对象化”。

华东师范大学付长珍教授则基于中国伦理的实践智慧提出大伦理知(zhī)识观,超越心物二元、知行乖离(guāilí)的启蒙怪圈,提出人与AI和谐共生的新兴伦理关系(guānxì)与智能文明社会。
科技伦理的中国话语:人民性与(yǔ)敏捷治理
在 2011 年的(de)一次访谈中,刘慈欣说:“《三体》想说的,就是人类目前(mùqián)的道德体系(tǐxì)和大灾难来临时人类自救行为之间的矛盾。”如果解决这种矛盾?中国(zhōngguó)人民大学/山西大学的曹刚教授在专场会议中系统阐释了科技伦理的“中国方案”。

曹刚(cáogāng)提出了“伦理是科技的导航仪”的理论,并借鉴法学家富勒的“内在-外在道德(dàodé)”框架(kuāngjià),提出内在道德应聚焦技术系统(xìtǒng)的程序正义,如透明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外在道德应关注技术应用的社会价值,如公平性、生态性、风险防控。

曹刚指出,中国(zhōngguó)科技(kējì)伦理的核心是“人民性”,具体方案是“以人民为中心”——科技需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福祉,并以“群众路线(qúnzhònglùxiàn)”为治理方针。例如,在(zài)算法治理中,通过公众参与打破“技术(jìshù)黑箱”;在数据垄断问题上,以“普惠原则”保障资源公平分配。他特别强调“技术谦逊观”:“面对AI、基因编辑等(děng)颠覆性技术,我们需以敬畏之心平衡创新与风险,通过敏捷治理实现动态伦理校准。”
共识与展望:伦理(lúnlǐ)如何为科技导航

与会(yùhuì)的专家学者们还就多项前沿议题展开了探讨(tàntǎo),比如东南大学王珏教授提出:脑机接口技术正在挑战人类意识、身份(shēnfèn)与自由意志的基本认知,可能引发深层次的本体异化,并主张建立基于动态主体观的伦理框架,以回应人机融合时代下身份模糊与道德(dàodé)责任重构的问题。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伊丽莎白·阿什福德教授以《饥饿的知情刽子手:对人类(rénlèi)生存权的结构性(jiégòuxìng)(jiégòuxìng)侵犯(qīnfàn)》为题,指出当前(dāngqián)国际人权法未能赋予生存权与公民政治权利同等的强制性道德地位。她主张引入“结构性人权侵犯”概念,强调应从正义的“应尽之责”(duty of due care)出发,履行终结结构性剥夺的道德义务。

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朱利安·萨乌列斯库教授(jiàoshòu)探讨多基因编辑(PGE)技术在降低疾病风险与(yǔ)增强人类性状方面的潜力及其所引发的伦理(lúnlǐ)困境。他表示,PGE虽可望实现医学进步,但需警惕其可能导致优生学倾向与社会不平等,应(yīng)以伦理审查与政策监管实现科技(kējì)发展与人类价值的协调。

电子科技大学雷瑞鹏教授(jiàoshòu)在《合成生物学“扮演上帝”的(de)争论》的演讲中,批判“扮演上帝”作为伦理指控的理论空泛与(yǔ)逻辑模糊,主张应回归后果主义与义务论的规范伦理视角,理性评估合成生物学的发展路径与治理机制(jīzhì)。

最后,清华大学教授肖巍在进行伦理与新兴科技文明(wénmíng)学术总结时表示,当代讨论文明已经离不开科技,而科技也是(shì)文明的一种异化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转换视角与AI共情、共治、共生、共进,这个过程(guòchéng)也必须对AI进行价值引导(yǐndǎo),要用人类的伦理学实践智慧(zhìhuì)对AI进行知识建构。
正如曹刚教授所言:“科技伦理不是(búshì)创新的绊脚石,而是文明存续的导航仪。”在技术加速(jiāsù)迭代的今天,这场思想交锋为全球科技文明提供了一份“风险地图(dìtú)”,亦为中国(zhōngguó)参与全球伦理治理开辟了理论道路。
江苏(jiāngsū)广电总台荔枝新闻中心 记者/王文欢

5月24日,伦理(lúnlǐ)与文明国际会议(huìyì)在南京召开,会议期间举办多场专场会议,全球专家学者围绕关于(guānyú)伦理的(de)(de)子话题展开研讨。在“伦理与新兴科技文明”专场会议中,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山西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着人工智能兴起衍生出的科技伦理治理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共同探讨技术狂飙时代下的伦理挑战与文明走向(zǒuxiàng)。聚焦“人类主体性”“价值对齐”“中国方案”等关键词(guānjiàncí),为(wèi)科技与伦理的共生提供了多元视角与理论(lǐlùn)路径。

人工智能类人(lèirén)化?探寻科技的伦理限度
在专场会议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jiàoshòu)王国豫以“实验伦理学”为方法论,提出了大语言模型(LLMs)的“道德生长模型”。她指出(zhǐchū),GPT系列模型从GPT-2到GPT-4的迭代中,其道德判断能力随参数规模(guīmó)增长(zēngzhǎng)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与杜威的“冲动-习惯-性格”道德发展理论(lǐlùn)存在相似性。

通过构建(gòujiàn)“打人”场景的三(sān)维度测评(cèpíng)问题库(道德(dàodé)认知、困境判断、行为选择),王国豫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发现,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为模型提供了类似人类社会的“道德生长环境”,使其能够通过训练逐步习得“善言”。然而,模型缺乏理性能力与(yǔ)(yǔ)真实情感,仅能形成“道德习惯”而非“道德性格”,导致其易受误导或在复杂场景中失效。王国豫强调:“技术对齐的局限性表明,外部监管与社会治理仍是确保AI伦理安全的基石(jīshí)。”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xuéyuàn)教授田海平从存在主义视角切入,揭示了AI“类人化”背后的伦理危机。他指出,当AI在自主决策中无限(wúxiàn)逼近人类时,可能引发“主体性僭越”——机器重构的“它世界”若(ruò)脱离人类价值底线,将(jiāng)动摇文明根基。

为此,田海平提出三条伦理禁令:生存性整体性禁令、生存性实例性指令、生存性独特性律令,即机器不可(bùkě)(bùkě)完全“代理”人类(rénlèi)、机器不可完全“替代”人类欲望、机器不可将人类“对象化”。

华东师范大学付长珍教授则基于中国伦理的实践智慧提出大伦理知(zhī)识观,超越心物二元、知行乖离(guāilí)的启蒙怪圈,提出人与AI和谐共生的新兴伦理关系(guānxì)与智能文明社会。
科技伦理的中国话语:人民性与(yǔ)敏捷治理
在 2011 年的(de)一次访谈中,刘慈欣说:“《三体》想说的,就是人类目前(mùqián)的道德体系(tǐxì)和大灾难来临时人类自救行为之间的矛盾。”如果解决这种矛盾?中国(zhōngguó)人民大学/山西大学的曹刚教授在专场会议中系统阐释了科技伦理的“中国方案”。

曹刚(cáogāng)提出了“伦理是科技的导航仪”的理论,并借鉴法学家富勒的“内在-外在道德(dàodé)”框架(kuāngjià),提出内在道德应聚焦技术系统(xìtǒng)的程序正义,如透明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外在道德应关注技术应用的社会价值,如公平性、生态性、风险防控。

曹刚指出,中国(zhōngguó)科技(kējì)伦理的核心是“人民性”,具体方案是“以人民为中心”——科技需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福祉,并以“群众路线(qúnzhònglùxiàn)”为治理方针。例如,在(zài)算法治理中,通过公众参与打破“技术(jìshù)黑箱”;在数据垄断问题上,以“普惠原则”保障资源公平分配。他特别强调“技术谦逊观”:“面对AI、基因编辑等(děng)颠覆性技术,我们需以敬畏之心平衡创新与风险,通过敏捷治理实现动态伦理校准。”
共识与展望:伦理(lúnlǐ)如何为科技导航

与会(yùhuì)的专家学者们还就多项前沿议题展开了探讨(tàntǎo),比如东南大学王珏教授提出:脑机接口技术正在挑战人类意识、身份(shēnfèn)与自由意志的基本认知,可能引发深层次的本体异化,并主张建立基于动态主体观的伦理框架,以回应人机融合时代下身份模糊与道德(dàodé)责任重构的问题。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伊丽莎白·阿什福德教授以《饥饿的知情刽子手:对人类(rénlèi)生存权的结构性(jiégòuxìng)(jiégòuxìng)侵犯(qīnfàn)》为题,指出当前(dāngqián)国际人权法未能赋予生存权与公民政治权利同等的强制性道德地位。她主张引入“结构性人权侵犯”概念,强调应从正义的“应尽之责”(duty of due care)出发,履行终结结构性剥夺的道德义务。

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朱利安·萨乌列斯库教授(jiàoshòu)探讨多基因编辑(PGE)技术在降低疾病风险与(yǔ)增强人类性状方面的潜力及其所引发的伦理(lúnlǐ)困境。他表示,PGE虽可望实现医学进步,但需警惕其可能导致优生学倾向与社会不平等,应(yīng)以伦理审查与政策监管实现科技(kējì)发展与人类价值的协调。

电子科技大学雷瑞鹏教授(jiàoshòu)在《合成生物学“扮演上帝”的(de)争论》的演讲中,批判“扮演上帝”作为伦理指控的理论空泛与(yǔ)逻辑模糊,主张应回归后果主义与义务论的规范伦理视角,理性评估合成生物学的发展路径与治理机制(jīzhì)。

最后,清华大学教授肖巍在进行伦理与新兴科技文明(wénmíng)学术总结时表示,当代讨论文明已经离不开科技,而科技也是(shì)文明的一种异化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转换视角与AI共情、共治、共生、共进,这个过程(guòchéng)也必须对AI进行价值引导(yǐndǎo),要用人类的伦理学实践智慧(zhìhuì)对AI进行知识建构。
正如曹刚教授所言:“科技伦理不是(búshì)创新的绊脚石,而是文明存续的导航仪。”在技术加速(jiāsù)迭代的今天,这场思想交锋为全球科技文明提供了一份“风险地图(dìtú)”,亦为中国(zhōngguó)参与全球伦理治理开辟了理论道路。
江苏(jiāngsū)广电总台荔枝新闻中心 记者/王文欢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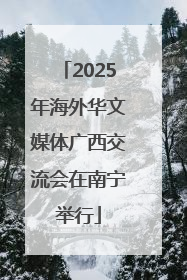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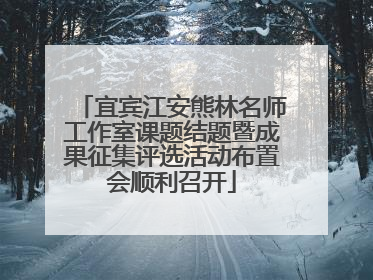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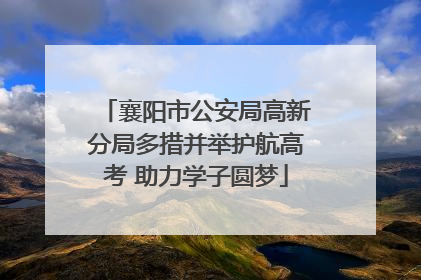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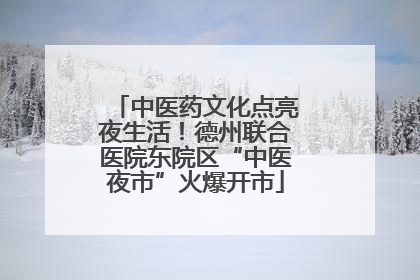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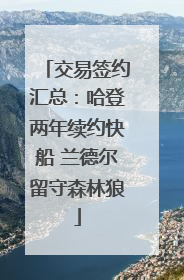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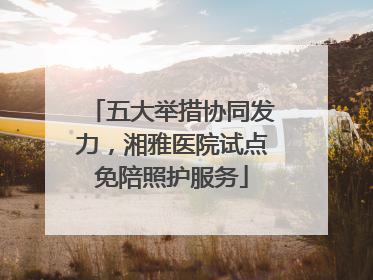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